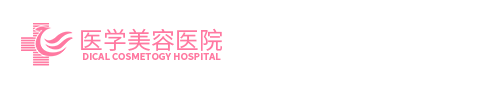安博体育游戏

从留存的照片来看,这位身材干瘦、戴着眼镜的摄影师,与影片中的伊藤秀夫高度神似。更为重要的是,《东京日日新闻》1937年12月13日刊登的“百人斩竞赛”照片及18日刊登的“南京入城式”照片以及朝香宫鸠彦等高官在南京故宫机场为日军战死者召开“悼亡会”的照片,均出自他手。与伊藤秀夫不同的是,佐藤振寿并非正式军人,而是供职于《大阪每日新闻》的摄影记者。二战期间,除了日本军方自己的摄影班外,还有大量报社所属的摄影记者跟随日军到前线进行拍摄,为本报提供第一手的新闻照片,佐藤振寿便为其中之一。1937年11月,时年24岁的佐藤振寿来到中国,开始跟随日军101师团进行拍摄。从11月29日开始,佐藤振寿跟随日军经无锡、常州、丹阳、句容一线日进入南京城,这一路见闻后来被其写入回忆录《步行随军》中。
并非拿枪,而是手持相机和纸笔,佐藤振寿这样的随军新闻记者在战场上有自己的一套目的与行事方法。受令于报社在前线附近设立的分社或支局,同一报社的摄影师、记者、联络员和无线电技师在战场上统一行动,跟随在日军后边寻找热点进行报道,同时还要和同行展开竞争。佐藤振寿在回忆录中自认是个要和军人打交道的“老百姓”,出发前除了粮食和胶卷外,还在旅行包里塞满了香烟,用以和军官搞好关系。出发当日,在常州城外,佐藤和同事浅海拿着香烟向两位军官请求采访,对面却反过来请求为他们拍摄照片,还谈起了二人正在进行的“比赛”——这就是“百人斩”竞赛,这两名军官则是日军第16师团第9联队的大队副官野田毅与炮兵小队长向井敏明。结束拍摄后,佐藤振寿和同伴们继续动身前进,日军每攻占一城,佐藤振寿就会以城墙或标志性建筑为背景,拍下高呼万岁的日本兵。哪家报纸的消息最快,照片最好,也成为了报社间竞争的焦点,而“头奖”毫无疑问是第一个进入南京。因此,即便还有中国守军的激烈抵抗,记者们还是纷纷“物色”一支自己认为能最先攻入南京的部队,冒着生命危险紧紧跟随其前进。
与片中伊藤秀夫的结局不同,佐藤振寿在1938年初即归国,后在1941年10月因病辞去在《大阪每日新闻》的职务,二战结束后又继续从事摄影工作,最终在2008年病死。2022年,《每日新闻》推出了一份题为《残像:战争的记忆与记录》(《残像・戦争の記憶と記録》)的特别报道,介绍了包括佐藤振寿在内的数名曾于二战期间为《东京日日新闻》及《大阪每日新闻》供稿拍摄的摄影记者及其经历。令人意外或是说也并不意外的是,“从不谈论战争”成为了这群摄影记者在战后的通常做法。佐藤振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未谈及他如何解读战场上的所见景象。他也从未谈及他对战争的看法,以及他如何看待自己以及报纸在报道战争中的责任。佐藤振寿的长子佐藤尹一在接受采访时称其父“从来不谈‘理论’”,而是坚持战场摄影师的身份,以“眼见为实”作为唯一的立场。
翻看佐藤振寿的回忆录,他并不回避他作为摄影师在南京工作时的狂热,尤其是急切地想成为最早入城的摄影师,更为能够报道日军入城仪式而感到荣耀。同时他也忠实记述了——或是说反复强调了这是他“有把握”“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即12月14日日军第9师团伊佐部队在国军88师营地对俘虏的杀戮。他甚至还不吝以尖锐的笔触进行描写:“实行枪杀与刺杀的日本兵们脸部都扭曲着,难以想像他们是正常人。他们似乎极为亢奋,已进入了一种疯狂的境界。”他也不敢拍照记录这一幕,因为“如果拍了照片,说不定我也会被杀。”但是这种不愿逾越“雷池”一步,绝不对日军罪行发表更多意见的做法,的确很难说是明哲保身还是内心情感复杂——或是兼而有之。而另一件事更能表现出佐藤振寿的这种矛盾,即便他亲手为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拍摄了“百人斩”竞赛照片,但他始终强调他并没有看到两人动手杀人的瞬间,因而他的照片不能证明二人负有罪行。甚至于他为二者因为这张照片“遭意外杀生之祸”感到歉疚和哀悼。2004年,已91岁且身患重病的佐藤振寿作为证人出席了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家人诉《每日新闻》的庭审现场。面对律师的询问,佐藤振寿仍然只承认他拍摄了照片,而并没有看到二人亲手杀戮。佐藤的证言是否对判决有所影响虽不得而知,但右翼势力此番妄图通过诉讼方式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行为最终没能得逞。
毫无疑问,从战后的所做所为及其公开的表达来看,佐藤振寿始终以“尊重事实”或者说“坚守原则”的形象示人。这甚至使他同时收到了左右两派的赞许。长期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称佐藤对日军暴行的记述可信度很高,“是一份宝贵的记录”。曾任安倍内阁防卫大臣,长期为日本二战罪行开脱翻案的右翼政客稻田朋美则满意于佐藤在“百人斩竞赛”事件上的模棱态度,称他“会仔细整理事实、说话很有条理”。事实上,不只是佐藤振寿,众多曾随日军报道的摄影师和记者都抱持着这种“有限承认”的态度。曾任《中央公论》社驻华中记者的石川达三,于1938年1月进入南京报道。同年3月,他冒着巨大风险发表了反映日军在华暴行的小说《活着的士兵》,并因此被判刑。石川达三在战后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并曾于50年代率团访华,多部作品被翻译引进,成为了在中国有重要影响力的日本作家。
但就是这样一位反思战争且与中国关系良好的名人,在南京大屠杀上却始终采取着一种模糊甚至否定的态度。他强调他入城时只看到一片废墟,而没有目击到直接的屠杀场景。他承认他的确将日军在中国的残虐行为加工后写入了小说,却否认“南京事件”的存在。甚至还有更多的日本随军记者完全否认大屠杀的存在。战争的废墟、死一般的宁静、“混浊得像是酱汤的河水”是有的,数量庞大的中国难民和俘虏也是有的,但是一谈及屠杀的场面,就只剩下“只看到几十具尸体”“这就是战争”“没看到杀戮的瞬间”或是干脆什么不曾有过了。以致于日本右翼乐于通过这些人的回忆,打造一个“东京审判之前从未听说有过南京大屠杀”的荒谬主张。这到底真的是个体经历的差异、对历史真相一丝不苟的严谨,还是仅仅将前述当作救命稻草和挡箭牌,乃至根本扭曲事实,的确不得而知,但也不需指望谁的幡然悔悟。
在《南京照相馆》中,伊藤秀夫因不会冲洗照片,不得已只能就地寻找会冲洗技术的中国人,由此开启了电影的整个故事。而片中出现的,大量被盖上“不许可”图章的照片,成为了主角团们最后舍命也要带出的日军罪证。这些情节设计与历史稍微有些不同,片中吉祥照相馆的原型华东照相馆,最初是一名日本军官到店要求冲洗两枚胶卷,其中的暴行照片被学徒工罗瑾发现并暗中保存。而对于佐藤振寿、河野公辉这样的日军随军摄影师而言,拍摄出来的底片要经过严格的保密和审查。在距离前线不远时,佐藤振寿会在每天傍晚回到设在上海虹口租界内的报社上海支局,底片由租界照相馆冲洗后附上说明用轮船送往长崎。而在跟随进军期间拍摄的底片,则会第一时间由联络员运往上海,随后空运回日本本土。这些照片随后还要经过陆海军机构的审查,通过后方可见报。
其中除了武器装备参数、伤亡事故、军队调度、高级军官相貌等涉及军事情报的照片外,第12条规定“对我军不利的新闻”;第13条规定“有关俘获、讯问中国士兵或中国人的新闻照片中,含有虐待嫌疑的内容”;第14条规定“关于虐待的新闻照片,但若是展示中国士兵或中国人的残虐性的内容,则不在此限”。在这样的审查制度下,唯有怎样的照片能成功登报自然可想而知。在日军暴行平息、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后,逃难民众又陆续回到南京。佐藤振寿于此时拍摄了一些街道秩序井然、日军与民众一起笑对镜头的照片,成为日军“仁政”和“皇道”的展示,其中的讽刺意味不用言说。甚至于时至今日,日本右翼仍然拿着这些“检阅济”的政治宣传照片,叫嚣着南京大屠杀不存在。
幸运的是,这种严苛的、为掩盖罪行服务的审查制度,最终没能完全得逞,大量的“不许可”照片得以保存到战后并重见天日。日本战败前夕,军部下令各报社销毁一切可能被当作战争见证的照片资料。此时大阪每日新闻社已经积攒有150册、近50箱军方退回的“不许可”照片。面对销毁令,众多报社都选择执行,日本同盟通讯社(今共同社)就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内将所有的底片与照片挖坑焚烧。但或许是出于对摄影职业的执着、或许也有对战争的些许反思,时任每日新闻大阪本社摄影部长的高田正雄说:“同事们豁出性命拍来的宝贵史料照片,能烧毁吗?!”带着部分同事将这些照片藏匿于地下室,由此成功保存了一部分照片。每日新闻社后以“不许可写线年将这部分照片分成三册出版。在泛黄的相簿上,黑白照片盖着颜色已浅的“检阅济”与“不许可”,旁边还有手写的照片简介或不通过说明,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企图隐瞒真相、欺骗世人的铁证。这一重要材料问世后也迅速被引入国内,选编入各种史料汇编之中。
随着电影的热映,“南京照相馆”的历史原型华东照相馆,以及接力保护“京字第一号”罪证的罗瑾与吴旋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影片结尾审判谷寿夫等战犯,法官传证物时抑扬顿挫的一段判词,就取材于上面这段《南京市民吴旋呈送日军暴行照片呈文》。虽然现实和电影中主角团以生命接力,最终成功将照片传出的情节有所不同,但却同样令人感动,甚至更有一分足以令人惊叹的传奇色彩。华东照相馆学徒工罗瑾洗印收集罪证照片后,冒着巨大风险将相册随身藏匿三年。1941年初,为了躲避汪伪政府的一次搜查,罗瑾将相册藏匿于南京毗卢寺厕所的墙洞中。几日后罗瑾发现相册不翼而飞,以为其已经落入汪伪警察手中,于是连夜逃走。万幸的是,真正拿走相册的是偶然发现它的另一位爱国青年吴旋。吴旋继续守护了这个来历不明的相簿六年,直至1947年南京国民政府征集日军罪证时将其交出,遂即成为了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京字第一号证据”。后来在1993年,早已定居福建大田的罗瑾回老家南京祭祖,期间偶然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才发现展厅里这份已经丢失了52年的相簿,并在两年后与他从未想过的接力吴旋重聚。两人舍命保留的这16张照片,在2015年作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一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文献遗产当中。
在影片带来的讨论中,有一种声音强调最早揭发日军暴行,让全世界关注南京真相的,是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约翰·马吉拍摄的105分钟胶片。这些胶片一共有8卷,由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牧师乔治·费奇冒着生命危险藏在大衣夹层中带出南京。1938年4月,胶片内容和其他来自南京的影像开始在美国《生活》杂志等媒体上陆续刊登出来,引起举世震惊。有人认为,约翰·马吉等外国友人的义举,从影响上要更甚于罗瑾、吴旋,理由是前者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与援助,在东京审判中,马吉亦出庭作证,其录像也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理的关键证据。如果这是出于善意的提醒与补充,借电影热映之机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这群曾为中国抗战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国际友人,当然无可非议。
【1】关于《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和现在的日本《每日新闻》的彼此关系:由于三者在相关历史文献中频繁出现,因此有必要阐明它们的彼此关系,以免错乱。《大阪每日新闻》常被时人简称为“大每”,而《东京日日新闻》则被称为“东日”。二者均在19世纪70年代创刊,原本各自经营,直到1911年“大每”收购“东日”,由此二者进入“一社两报”的经营阶段,各自保留原名并分开两地出版,实则已是一家。1943年二报正式合并,统一改名为《每日新闻》,后虽曾在战后又恢复“东京日日新闻”的旧名,但自1948年起再度统一为《每日新闻》且沿用至今,目前仍是日本的全国性新闻媒体,总部位于东京。因此可以解释为何佐藤振寿是《大阪每日新闻》的雇员,其作品却刊登在《东京日日新闻》上。